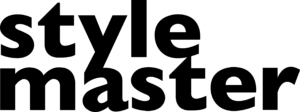即使走在台北街頭,我經常不自覺的嗅空氣的味道,嗅哪裡傳來咖啡的香味。培養我訓練出這種直覺的是小時候鄰居沈伯伯。
他來自上海,與我爸爸同為中央造幣廠的員工,我們兩家共用門口的小小一塊騎樓,五月起晚飯後他會搧著扇子坐在門口,等人找他聊公事、國事、天下事,有時跟我這種小把戯聊點知識。
最初聞到一種香味,不知哪裡傳來的,看到我家的華僑房客在廚房將熱水沖進他杯子,我問是什麼?他笑著說:小朋友不能喝。
沈伯伯摸摸嘴唇上的鬍子說,那叫咖啡,你想喝,明天晚上做完功課來,我請你喝。
第二天晚上他拿個小碟子,上面是個瓷做的小杯子,杯子裡散發的正是勾引我的香味。他說,張小朋友,兩塊方糖可以嗎?
那晚我尿床,尿得──用我媽的說法,漫山遍野。沈伯伯被沈媽媽連續罵了
好幾天,不過他還是悄悄朝我眨眼睛:咖啡的味道不賴吧。
想起里斯本巴西人咖啡館前的詩人佩索亞銅像,他戴高帽子翹一條腿,彷彿等他的咖啡,他也有撮小鬍子,我聽到他說:小朋友,兩塊方糖?

高中,民國六0年代初,在西門町的小巷子內,我們抱著書包小心的按門鈴,彷彿隨時有人衝來以槍對準我:不准動。
沒人,沒槍。門後的聲音問:「哪位?」同學回答:「小屁。」
門開後,得爬很窄很陡峭的水泥樓梯到二樓,再打開一個小門,頓時煙如同霧霾般撲頭蓋臉的襲來。這間店經營四件商品:撞球、賓果機、香煙和咖啡。奇怪的組合。我不打球,不玩賓果,我坐到角落的機器旁,操作機器的女孩穿紅色短裙、戴比如今五十元銅板還大的白色中空耳環、頭髮燙得一邊向內捲成倒過來的問號。她叫莎莎,她問我要不要來杯咖啡。
我和小屁各捧一杯,卑微的縮著脖子吸烏黑的液體看大哥們打賓果、打開侖,直到有人大喊「條子,閃人。」我們放下杯子從公寓後面跳至一樓的巷子,一手扶穩軍訓大盤帽沒命的跑,書包幾乎飛得像飛機的尾翼。
後來有次我問莎莎,咖啡怎麼喝好?莎莎有頭神奇的短髮,用水梳得服貼的上學,風一吹再甩甩頭,瞬間爆炸的放學。「要心情對。」她嚼著口香糖,踩著阿哥哥舞步,左搖,右搖。「想喝咖啡的心情,喝了咖啡會平靜的心情。」
莎莎吹出個泡泡,身體繼續的左搖,右搖。我不是很懂她的心情。
想起北海道札幌圓山公園前木造老樓的森彥咖啡館,夏天被樹葉罩得很龍貓氣氛,坐在二樓捧著咖啡看窗外的綠,心情變得很平很平,平得禁不起海鳥觸碰的海面。
大學時期,系裡的語音學教授原土洋有很重的咖啡癮,下午準三點,他的研究室傳出濃郁的香氣,我們拉出襯衫下擺抹抹杯子搶著上樓,每人分一口,喝下後都做出「啊」的滿足表情。
他領我們到輔大對面的柏拉圖咖啡館邊喝邊上課,日文系的咖啡文化是他帶出來的,英文系的詩人羅青有次叫住我:張國立,你們哪位老師煮咖啡,香死人。我們還去西門町喝了蜂大,喝了南美。很多年後很多學生忘了日文,沒忘記咖啡。好像咖啡使得念書變得輕鬆與優雅,像飛翔時需要雲朵,像做夢需要滿天的星星,像駛進愛琴海時需要島嶼。
一九九幾年的初夏,我坐在愛琴海密克諾斯島的漁港邊,綁花布頭巾的老太太倒出我杯中的咖啡渣算命,用英語單字對我說,你很久以前就喜歡咖啡,很久以後還會。
當記者期間,和老SOGO百貨地下二樓的UCC虹吸式咖啡結下緣分,中午先去喝完咖啡看完三份報紙,充滿幹勁的跑新聞去。它開張了多少年,我去了多少年,從坐在吧台看報抽著煙等咖啡,到闢了吸煙室,到取消了吸煙室。人來人往,很多熟面孔隨著歲月老去,和我一樣,就是單純坐坐的享受時間從身邊飄逝。真的,看得到時間如煙霧般的存在,如晨霧般的擺動。當然不會去抓它,抓時間是很笨的行為,我抓的是咖啡杯。
有位美國作家寫的,咖啡是陪伴,當一個人在遠方,有了咖啡即不再寂寞。
奧地利的咖啡館華麗、典雅,有如訴說哈布斯堡王朝於一六八三年擊退鄂圖曼土耳其大軍的榮耀。戰後一名波蘭商人於鄂圖曼軍營內發現咖啡豆,開啟了歐洲豐富的咖啡史,令人情不自禁想像炮火中,端著咖啡杯的兩撇翹鬍子的軍官。

寫作與看書組成我人生的一部分,總會沖一杯咖啡再打開電腦或書,需要它溫暖人心的香氣、入口後湧出的另一股更深層的味道。咖啡渣捨不得扔了,留下倒進特別挑的碗內,讓它消失的腳步慢些。日文裡有組漢字「殘響」,回音的意思,但動詞不同,一用「殘」,一用「回」,咖啡當然是殘,心情一點點的沉澱。
早晨的咖啡喚醒靈魂,下午的咖啡撫平靈魂。我早上幾乎不喝咖啡,讓靈魂慢慢的醒,到下午喝時,靈魂溫馴得能隨杯內的黑色液體泛動,而後緩慢的於「殘」之中不知不覺的消失。
工業革命時倫敦賣咖啡小童腳卻快,他們提著小的炭爐一早奔波於仍昏暗的石塊拼成的街道,現煮的咖啡,出門上班或上工的男人付出一枚硬幣換得面對新的一天的勇氣。
不太喜歡機器煮的咖啡,它不像該和機器發生關係的植物,它不適合焦慮或過度快樂,殘得像畫家畫海平線,一直一直的畫到紙張的盡頭。
紙張的那一邊,海的那一邊,海明威寫著,男孩從小店買來一杯咖啡對老漁夫桑提亞哥說,你得喝了咖啡再出海。已連續八十四天未捕到一條魚的老人拿起杯子慢慢的喝,不受年齡限制的友情在這杯咖啡裡如漣漪般的綻放。
我曾認識一位老人,他給了我咖啡,是啊,透過咖啡,我得到太多的關懷,於是任何朋友找我見面,我總說喝杯咖啡去,談話可以慢慢的開始,不急著登上火箭去火星。

火星曾有間咖啡館,在人類望遠鏡看不到的角落,如果沒有,火星有存在的意義嗎,火星不寂寞嗎?
我記得火星的那間咖啡館,有好長的窗戶,能坐十幾人,用木頭支起玻璃,讓來自銀河的冷風吹進來。沖繩海邊有這樣的一家,但比火星的小。
窗前是木頭的桌面,坐在高腳椅倚著桌面看菊紅的天空會不會突然冒出幾個在半空噗的破掉的氣泡。
後面的吧台是位瘦高的月球男孩,拿彎曲的長嘴壺往濾紙內的咖啡內順時鐘或逆時鐘的倒,冒出的熱氣糊了他圓形的氧氣罩,於是他抬頭看坐在窗前來自海王星的女孩背影。女孩梳兩條長辮子,白色圓形的帽子突出在今天比較紅的的天空。
喔,我坐在女孩隔兩個位子的左邊,也看外面天際線處好幾顆不同顏色的星球,也看到飄起的汽泡,偶而側頭也看到女孩的辮子。在火星,我有足夠的時間與心情等待咖啡。
是的,火星一定有家這樣的咖啡館,每天上午十一點開門,希望今天的甜點有冥王星來的地獄鬆餅,灑滿脆脆的巧力克片。
咖啡適合期待的心情……⋯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stylemaster第65期】
購買方式:實體通路誠品、金石堂、網路博客來皆可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