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提供/米倉影業
魏德聖導演新片 《BIG》年底上映,是台灣首部結合動畫的醫療主題電影,這也是導演首次嘗試溫馨的家庭題材,片中以兒童癌症病房「816」切入,講述六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從彼此衝突到互相扶持的溫馨故事。自12月1日上映以來網友好評口碑不斷,在醫護界也獲得許多正面評價,甚至很多人從片裡的溫暖獲得了滿滿的正能量,這回導演魏德聖也接受了我們專訪,與我們聊聊創作《BIG》的契機與拍片時遇到的困難及收穫。
-1024x683.jpeg)
兒童癌症不像成人癌症由後天不良習慣、壓力等因素導致,而是先天來自遺傳或是不知原因的細胞病變。當初會想拍一部以兒童癌症為出發的電影,是起源於20多年前導演在電視紀錄片中訪談一位已截肢康復的女癌童,當時為了避免癌細胞擴散,所以截下一隻腿,必須拄著拐杖走路,但她依舊非常樂觀,並把過去還在病房治療的日子形容得像是在學校的某個班級,「那時候我對兒童骨癌並沒有什麼印象,完全是空白的,我的想像是灰暗陰鬱的,我就依照我的想法問他,那你們在癌症病房都在做什麼呢?治療時間之外都在幹嘛?」小女孩回答他:「就玩啊、聊天阿、打撲克牌啊,或者是到隔壁房找朋友。」導演當時聽完心想:「這感覺不像是病房吧,很像是某個學校的班級而已啊,跟一般孩子沒什麼兩樣,但後來我想想對啊,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不管生病多嚴重,只要他還能動,他還是會想要玩。於是我又問他,難道你們在治療的過程不會痛嗎?不會哭嗎?」小女孩說:「還是會哭,因為會痛,但不會鬧,因為鬧沒有用,鬧還是要治療,爸媽看了只會更難過而已。」
-1024x683.jpeg)
沒想到一個小孩面臨癌症是這樣的成熟反應,而最令導演印象深刻,也是他寫這個劇本的契機是,他問這位小女孩:「那你在癌症病房裡面應該有遇過走掉的孩子,或者是快接近死亡邊緣,治療好幾次都好沒用,他們在治療的過程中,難道都不會想說算了,不要治療了,去當小天使吧?」小女孩愣了三秒後回答他:「我在癌症病房這麼久的時間,進出了兩次,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不想活的孩子,每一個孩子不只是想活,也相信他們可以活著。」這句話讓導演聽了很震撼,嘆道這麼弱小的孩子,他們的生命力是如此地堅強,「那這麼多的大人們是怎麼了?當面臨了生活或社會上的壓力,不是想逃避或是想要自殺,但是這些生病的小孩子每天都在求活,而且在活的過程裡都在求精彩,求快樂,而且相信自己會活著,就是這個東西刺激了我!」這也令導演的心中萌生了創作這個題材的想法。
-1024x683.jpg)
《BIG》主演群多達 21 人,除了大量的群戲與故事線需要兼顧,還有許多表演經驗尚淺的小演員,拍攝過程充滿挑戰。「要拍這麼多演員的戲,它本身就是很大的難題,特別是要如何兼顧到每一個演員的主戲,他們必須要有所表現,除此之外,在大堆頭出現的那場戲,我們該如何走位,運鏡的方式去帶到每一個人而不漏掉某些演員的戲,導演的功課必須要作足,處理上就要事先做好準備,不適合臨場反應的拍攝方式,現場只能應付意外。」
-1024x683.jpeg)
除了大人以外還有許多小孩演員,而這些小孩的耐心也有限,必須要在他們有限的耐心裡完成拍攝;而對導演來說最難的一項挑戰就是要將所有專業的演員聚在一起,「光時間大家都要喬到可以,光這點就是一個大難題了!已經敲好的時間就不能夠再有閃失,一定要一次解決,對我來說這麼大的群戲,有大人、有小孩,並且設定不同年齡層,不同社會階層的這個組合,演員的背景也不同,有些是歌手出身,有些是表演出身,每個人扮演的角色也不見得跟大家既有的想像一樣,所以要怎麼把這麼多大大小小的演員聚集在一起,並且在表演上維持一個頻率,這是最難的,不能讓誰特別誇大,也不能讓誰特別地尷尬。」
而片中六位童星的演出也讓人驚艷,童言童語讓劇情增添輕鬆不少,如同導演所說:「在由孩子口中說出來單純卻又直白的話,有時更能震撼人心。」但要跟這些表演經驗尚淺的小孩們合作,導演又是如何辦到的呢?「這也是我們這個計畫最大,也是最有趣的挑戰,其實我本來就很喜歡小孩子,我一直覺得自己跟小孩子是可以對話的,對他們來說,我是他們的朋友,我也把他們當自己的孩子看,所以我會跟他們用平起平坐的方式在溝通,我不會說你還小,你要聽我的,我會用朋友或是跟自己小孩子的角度去跟他們聊,與他們培養感情。」
與小演員們經歷三個多月的相處,讓他打趣表示「拍完可以開幼稚園了」,右為演員黃之諾。(米倉影業提供)-1024x683.jpeg)
而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有表演經驗的,針對這些小孩基本上就可以直接針對戲劇需求去跟他們做一些節奏跟細節的溝通,「但也因為年紀小的原因,表演的資料庫裝存的不多,所以我們經常要用帶入的方式給他們不同的情緒,甚至告訴他們一些表演的節奏,先怎麼樣再怎麼樣,哪個地方要慢一點,哪個地方要快一點?但他們的表演上我是都不用擔心的。」
至於年紀最小三個小孩謝以樂、滕韋煦、努拉,導演就會花比較多的時間多做陪伴,無論是聊天或是用玩樂的方式跟他們相處,「要讓他們覺得跟一群大人工作會很有成就感,並且還可以在遊戲過程工作,這就是我們創造的氛圍,也滿足這些小小孩生理上的需求。該吃的時候給他們吃,該睡的時候給他們睡,該給糖果的時候給他們糖果,不要百般刁難;在心理上的部分,如果他們表演的很棒,你要大力地稱讚他,如果表演的不好,哪個地方節奏不對,你也不可以跟他們生氣,你要跟他們用半開玩笑的方式說少了這個,或是是我這邊沒有弄好,你可以再幫我一次嗎?用這樣的方式讓他們感覺到成就感。」
表示拍攝《BIG》之後更了解如何與孩子相處,用已學會抱起孩子用說故事的方式了解他們的情況、安撫他們,左為演員滕韋煦。(米倉影業提供)-1-1024x683.jpeg)
在跟這些小孩演員拍戲的過程中,他們的天生無邪也感染到導演的內心,「如果小朋友在面對這麼多表演上的難題,都可以用遊戲的心態來完成這份工作,還有那些真正在病房裡,躺在床上還掙扎想要起來玩樂的孩子們,他們即使生了重病,即使生病很不舒服,只要他們能動,他們還是願意下床來玩,對比這些孩子,我們大人要學習的真的是太多了!若說要我從這些小孩子學習到什麼的話,就是純真樂觀,如果這一點我能好好學會的話,我應該也可以度過人生更多難關,擁有了安全感,全然地放心去面對挑戰。」
於電影《BIG》拍攝期間曾特別從日本來台探班,親自與導演、七位演員碰面。後排左2起為郭大睿、導演魏德聖、于卉喬,下排左起為滕韋煦、謝-1024x683.jpg)
值得一提的是,《BIG》也加入了動畫的形式,並由日本知名動畫導演新海誠的御用美術丹治匠擔任動畫導演,帶領日本、義大利、台灣動畫團隊,依照七位病童不同的特徵與角色設定,繪製七個專屬的動畫角色。為什麼會想加入動畫在電影中?導演認為:「我們常常跟一個病人說加油,因為他只能躺著在病床上被治療動手術,但我們看不見他在努力積極的那一面,所以我才會想說可不可以做出一些積極的動作,從小孩子的視角做出發,從他們的心裡重新建構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的畫面是動畫的話,我想那會是一場戰爭的畫面,用動畫來表現會更童趣一點。」
,圖為主要角色的動畫設計。(米倉影業提供)-1024x425.jpg)
而與丹治匠合作不是第一次,導演與他其實已經認識很久了,從《賽德克巴萊》就有合作製作過主視覺的氛圍圖,也參與了導演正在製作中的 3D 動畫片《達娜米》以及《臺灣三部曲》動畫片製作。「丹治匠團隊們很尊重我的想法,我也很尊重他們的技術,他們對自身的技術也是非常負責,所以我完全不用擔心,我就是提出我的概念跟我要的節奏,接下來就讓他們自己發揮。為了將動畫做到最好,他們甚至遠到義大利找了另外一組工作團隊,想要作出不同於以往的日本風格,試著創造一個台灣風格的動畫。那什麼是台灣風格呢?其實也沒有一個固定風格,丹治匠手法上把日式融合義大利式,應該就能創造出一個特別的風格,所以這次的動畫風格,我很願意稱為台式風格,因為它既不是純日式也不是純歐式,它就是兩個綜合起來的一個新的形式。」
的加入,期待他獨特的風格與創意能為電影《BIG》帶來全新的感受。(米倉影業提供)-1024x683.jpg)
丹治匠也在電影拍攝期間特地從日本飛來台灣探班,親自體驗本片拍攝的過程,並親自與七位飾演病童的演員碰面。他對於現場活潑又緊密的拍攝氣氛讓他感到十分難忘,訪談時他更大方分享對於魏德聖的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講究的人,同時又樂於嘗試各種不同的方法讓複雜的事情變得容易理解,我認為這並不容易,但他會毫不猶豫的去挑戰,這真的很了不起。」
六組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中,有夫妻失和、單親媽媽、離婚怨偶等等,拍攝的哪一幕最觸動導演?他回答每一組都有感覺,寫劇本就是把自己的某一部分給投射進去,「但不代表我只會投射到某一組人,是在不同的情緒上會投射在不同組合,我跟老婆吵架的時候會投射到黃鐙輝跟曾珮瑜,跟老婆比較冷戰的狀態時,我就會投射到范逸臣跟田中千繪那一組,這部電影我會站在比較憐憫的角度去看待每一組家庭的爸爸媽媽們,照顧者本身就是一個難扮演的角色,除了要陪伴,他們還要隱藏自己的傷心難過、自己的喜怒哀樂,刻意地要讓孩子可以愉快,可以健康,可以接受治療過程中的疼痛。」
因為鄭又菲(右)溫暖的舉動而對她改觀。(米倉影業提供)-1024x683.jpg)
但硬要選一組來講的話,導演笑說還是會對源源家偏心一點,「畢竟這是我創作的原點,無論如何都要活下來的創作原點,加上曾沛慈跟菲菲(鄭又菲)兩位的表演都非常貼近我想像中的樣子,甚至更超過我想像中的樣子,所以有好幾幕即使沒有說話,只是一個微笑,只是一個安靜日常的一個擁抱,我都會感到很不捨,光那樣的表演就會讓我思考,這樣的媽媽所呈現出來的堅強是真心還是佯裝,那樣的狀態反而會讓你更傷心,捨不得他們要面臨這樣的困境時還要強顏歡笑,站在這邊我是更有感一點。」
橫式.jpg)
「而另外幾場小朋友動手術前跟父母說:『爸媽我愛你。』李佳豫那個表演,明明是受不了要哭出來,但還是一個深呼吸轉過來一個笑臉,再回去捏捏孩子的臉,這些很細微的表演,好幾段我看了都會心酸!」
20年前的一個訪談種下機緣,直到20年以後電影《BIG》才正式開花,導演希望從小孩的視角來告訴大家他們是有多麽的勇敢,而不是用旁觀者的角度來告訴大家他們有多可憐;導演也將這長達20年的生命體會融入了故事裡,讓劇情更豐富感動,他也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不再充滿負能量,同時也被故事療癒了,也希望將這份感動傳遞給進戲院的觀影者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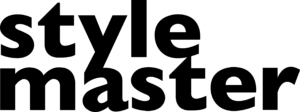
.jpg)



